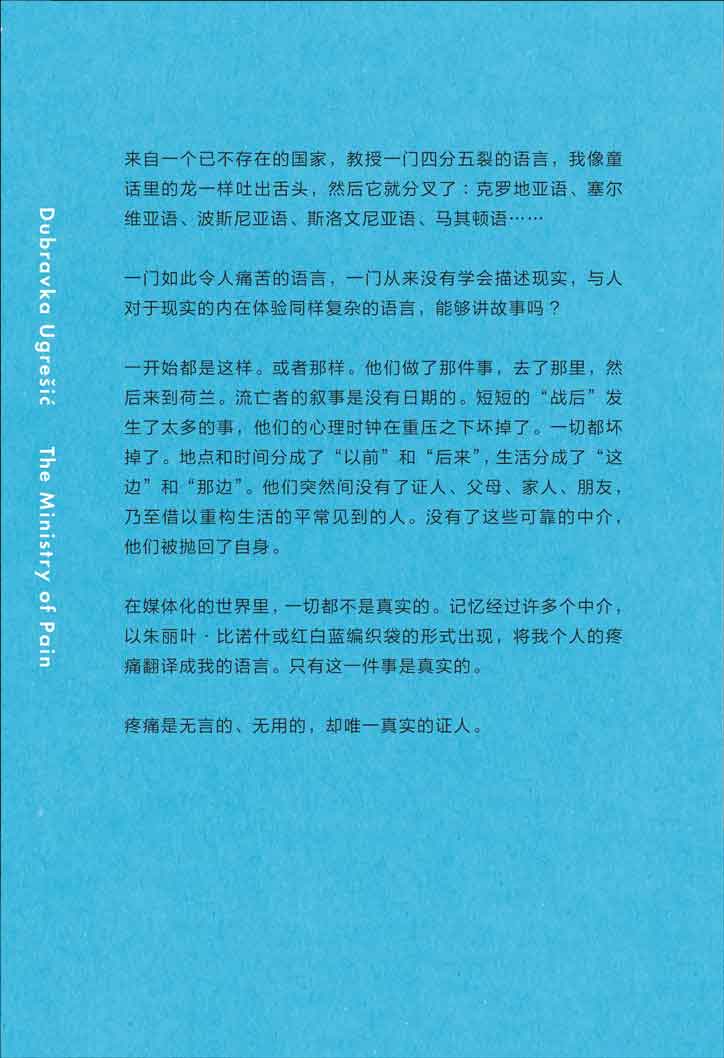| 疼痛部 | 收藏 |
后记
疼痛部 作者: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
生活有时是如此混乱,以至于你无法确定哪些事先发生,哪些事后发生。同理,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讲到了事情的结尾还是开头。自从来到国外生活,我就感觉自己的母语——用那位克罗地亚诗人狂乱的诗句形容,它是:
狂风,巨钟,回响,轰鸣,
雷霆,咆哮,回荡——
是结巴,是咒骂,是诅咒,或者是含混的、单调的、没有意义的卖弄辞藻。因此,在这个身边都是荷兰人、沟通要用英语的国家,我有时感觉自己在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。这并不简单。我死记单词,反复练习元音和辅音。这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:我表达不出我想说的意思,而我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又是空洞的。我会想到一个词,但不知道它的实际意思;或者,我感知到了一个意思,但找不到合适的词。我一直在想,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,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,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,它到底能做什么事呢?比如说,它能讲故事吗?
生活对我一直不错。我学会了拉窗帘。我甚至试着把它当成一件好事。我报名了荷兰语班。与许多同学一样,我会滥用第一人称代词ik。对初学者来说,世界是从ik开始的:Ik ben Tanja Lucič. Ik kom uit vormalige Joegoslavië. Ik loop, ik zie, ik leef, ik praat, ik adem, ik hoor, ik schreeuw……[荷兰语,意为:我叫Tanja Lucič。我来自南斯拉夫。我散步,我看,我生活,我说话,我呼吸,我听到,我尖叫……]就目前为止,我说的ik并无实质内容:就像是孩子的游戏;就像捉迷藏。人们常说,躲在开阔地是最容易的。躲在荷兰的山里。躲在生硬的i和k后面。
没错,噩梦又来了。我现在梦到的是单词,不是房子。在梦里,我讲的是一门没有顾忌、不可控制的语言,一门有阴暗面的语言,单词像玩偶盒里的小丑一样冲着我弹出来。它们通常是反映我的脆弱精神状态的单音节词。我用一把细齿梳梳理着它们。音拖得很长,包含着痛苦,是没有尽头的抱怨。我经常被痛苦的、像狗一样的呜咽声吵醒,是我的声音。在梦里,我的身边都是单词。它们像藤蔓一样绕着我生长,像蕨类一样迸发,像爬墙虎一样爬墙,像荷花一样舒展,像野兰花一样爬满我的身上。茂密的句子丛林让我无法呼吸。早晨起床时,饱受摧残的我说不清那繁多的词汇是惩罚,还是救赎。
但是,生活对我一直不错。保罗和金,那对雇我每周帮他们照顾四天孩子的美国夫妇,给我的工资相当丰厚。我成了摇篮曲和数字歌的专家:有我们的,有英语的,甚至还有几首荷兰语的。孩子们知道En ten tini, sava raka tini, sava raka tika taka, bija baja buf[计数童谣“Eeny, meeny, miny, moe”的以色列变体,名为“En Den Dino”。]。知道Eci peci pec, ti si mali zec, a ja mala vjeverica, eci peci pec[塞尔维亚童谣,意为:快来烧炉子,你是小兔子,我是小松鼠,快来烧炉子。]。他们知道Rub-a-dub-dub, three men in a tub: the butcher, the baker, the candlestick maker[英语童谣,意为:咚咚嚓咚咚,浴缸里有三个人:屠夫、面包师和蜡烛匠。]。还有Amsterdam, die grote stadt. Die is gebouwd op palen. Als die stadt eens ommeviel, wie zou dat betalen……[荷兰语童谣,意为:阿姆斯特丹,是个大城市,建在柱子上,要是倒下去,谁能赔得起……]保罗和金只要有机会就把我介绍给亲戚朋友:“这是塔尼娅,我家的保姆。前南斯拉夫来的。塔尼娅特别会照顾孩子。她对小孩确实有一套。”
我母亲也挺好的,如果挺好这个词合适的话。只要我打电话,她就来劲了。她会像孩子一样讲述自己的生活:先是拉一张投诉单子,然后讲她的糖尿病(她叫糖咒病)、她的关节炎、生活开销大……她从来不问我的事:我只是听取投诉的。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角色,渐渐习惯了我们间的单向度对话。我已经学会了不要太受伤。
戈兰的父亲不在了。“他们没准会把他塞进垃圾袋里的!”奥尔加在电话里哭着说。“垃圾袋!”他当时陷入昏厥,于是她叫了一辆救护车。但是,担架放不进电梯,护士只好把他裹在毯子里,从顶层十楼搬下来。几天后,他于医院去世。我打电话慰问时,她把事情全都讲了。“不过,人总归是要死的。”她补充了一句,声音很奇怪,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悲伤却麻木的句点。
安娜回到贝尔格莱德后只活了不到两年:北约轰炸该市期间,有一个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的摄制组丧生,安娜当时就和他们在一起。我收藏着她离开几个月后给我寄来的信。除了说自己找到了工作,日子过得不错以外,她还附上了一篇题为车站的短文,是献给我们虚拟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馆的一份迟来的藏品。文章用悲凉的语调描绘了贝尔格莱德的电车休息站,描写了各种声音、闷热的夏日黄昏、空气中的尘土味。“将它装进我们的塑料大包里吧,那个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大包。”她写道。这可爱中透着傻气的姿态触动了我。海尔特决定留在贝尔格莱德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,如何维持生计。他不时跟我通电话。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,我,一个外国人,是他与家唯一的联系。我还住在他原来的地址。
其他人似乎都过得不错。安特还是在城内各处演奏手风琴。他每周六都在北市场。人们会把钱投到他的帽子里,帽子是那里一名摆摊卖帽子的维罗维蒂察人送给他的。我们的人全都认识他。奈维娜嫁给了一个我们的小伙子,跟他生了个女儿。她在荷兰合作银行墨卡托广场分行上班。梅丽哈在萨拉热窝。她想办法要回了自家的公寓,把非法住户赶了出去。梅丽哈的父母与那座城市毫无关系:自从搬来这边,他们一次都没回去过。梅丽哈与一名达舍人同居,他创办了一家服务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。马里奥退学后进入了计算机图形行业。他也有孩子了,男孩。波班加入了本地的佛教团体,剃发食素,化缘为生。只有约翰内克还在大学就读。她的大女儿跑了,现在和她爸爸在波斯尼亚住。约翰内克心碎欲绝。塞利姆成了“极端穆斯林”,成天跟冯德尔公园的怪人们混在一块,嚷嚷着“我们波斯尼亚人要让那些塞尔维亚杂种都滚蛋,然后是克罗地亚人,那些欧洲人全滚蛋,还有美国佬”。据说,只来上过一两次课的佐勒分手了,因为要去加拿大,他自称是双重受害者——米洛舍维奇加上北约轰炸。不过,更可能的情况是他惹上了当地的塞尔维亚黑手党,分手是为了保命。
这些都是达尔科告诉我的,我有一天在瓦瑟纳尔附近的荒凉海滩偶遇了他。太超现实了。我差点儿没认出他:他浑身古铜色,头发成了淡黄色,戴着时尚太阳镜和随身听。他还骑在马上。他看起来就像一名CK模特,或者说是瘦弱版的CK模特。他告诉我,他正在上瓦瑟纳尔马术俱乐部的马术课。他以前就有一个朋友是美国富商,男的,在同性中很有市场。只不过,他即将脱离底层生活——他从来不隐晦这种想法——搬进常律会运河的一座宅子里。这要多亏他的朋友,掏了整整一百万给他买房。对了——是一百万美元,合两百万Guće……
“我发现自己喜欢骑马。”他说。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,说道,“报一门课吧,什么课都行——瑜伽,莎莎舞,随便——我跟谁都这么讲。只要能活动身体,都有大好处。”
“我在学荷兰语。”我说。
“好呀!”他说,好像在跟别处的别人说话。
这时,我在他的太阳镜上看到了我的倒影,结果顺着脊柱窜上来一股寒意:闪亮的镜片上有两张脸,没有一张是我的脸。
但是,最离奇的故事当属伊戈尔。人们都说他疯了。他一开始在前南法庭做译员;顺便说一句,我们这伙人里做这份工作的不止他一个。但是,他后来因为旷工被开除了。后来有一天,他被找到了——说他找到了自己可能更贴近真实——是在某座机场,在加尔各答、吉隆坡或者新加坡。人们说,他得了一种名字很好听的创伤后综合征,叫解离性赋格,和音乐里的赋格是一个词。这种赋格似乎是由突然出走引发的,持续时间从数日至数月不等。患者会完全失忆,赋格人只能自己造一个身份: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,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。当他们回归之前的生活时,他们会完全不记得赋格状态下的经历。谁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记忆失而复得的不可理喻的心理障碍。有心理医生主张,赋格障碍不是凭空发生的,而是由酗酒触发的。可能吧,但达尔科不记得伊戈尔是个酒鬼。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,如何维持生活。他可能回国了吧。其他人各走各的路,已经失联了。
“顺便说一句,”达尔科的声音有一点过于兴奋,“我有了一个新发现。”
“是什么?”
“歌剧!”他指着随身听说,“我爱死威尔第了。”
他停住话头,身子微微沉了沉,一道微弱的阴影划过他秀气俊美的娃娃脸。
“那一次跟乌罗什……”他说话吞吞吐吐,好像要从嘴里吐沙子似的,“晚饭后我们给你庆生那一次,记得吗?”
“记得。”我说。
“那个,我送他回家,我们……骑了一会儿马。乌罗什不是同性恋……我们都喝醉了……”
“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?”
他耸了耸肩。
“不知道……它一直困扰着我。”
在海牙前南法庭,文件越积越多,纸山越堆越高;庭审的录像带能铺满那个已经不在的国家的全境。每一次伤害似乎受到了真实、讽刺或怪异的处理——但总归是处理了。有些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,有些人不好——但也算是恢复了。就连疤痕都在消退。人人都有去处,有人发挥特长,有人勉力而为。生活发给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,但每个人总能找到某个地盘。死者与失踪者有待清点,许多恶徒依然逍遥法外,许多瓦砾有待清理,许多地雷有待拆除,但尘埃已经落定。生活继续了下去,至少就目前来看,这对每个人都好。
总有一天,元凶首恶会来到法庭,我一定会去看。他会穿着灰正装、白衬衫,打着鲜红的领带。领带与法官袍是同样的颜色。被告会坐在他的玻璃牢笼里,双颚紧扣,嘴巴呈倒U形。时钟会显示时间,但那不是审判庭外的世界的时间。我会震惊地发现,我在中间的这几年里已经忘掉了一切,我想不起那些曾经如此玩弄我们的生活的人叫什么。我会感觉距离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一百年,而不是九年、十年。我会用深重的恐惧感去直面自己的健忘。打着红领带的男人会讲一门我已经不会的语言。我甚至会记得下面这些细节:翻阅眼前的文件时,被告会像村里的小店主一样舔手指;他会仰起头,好像在嗅周围的空气,然后眯起眼看审判庭;在那一刻,我的眼神会与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交会;那双眼睛是黑色的,呆滞的,无神的;他紧扣的双颚和呆滞的眼神会让我想起北极熊;接着,他会抬起爪子,赶走鼻子周围的飞虫,继续空洞地盯着前方。
我有时会想起乌罗什,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。他带走了铅笔、本子和犹太小圆帽,一周七天,一天一份。他刷了牙,如果条件允许,他还会转向神圣的哭墙。他像会计一样出着汗,在纸片上写下悼词和祷词,卷成小筒后塞进石块的缝隙中。
“因为当你经历了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后,只有三种可能:你要么变好,要么变坏,要么像乌罗什那样,用子弹打穿大脑。我不知道属于哪一种,只知道自己躲过了子弹。”伊戈尔曾这样说。
我没有向达尔科透露,我对伊戈尔的了解要比他那天在海滩上告诉我的更多。比方说,我给警方录的口供从来没有到伊戈尔手上。来我家的警察肯定觉得为我解开手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倒也没错。我低估了伊戈尔的精明。
现在,伊戈尔和几个爱尔兰建筑工人搭伴。爱尔兰人手艺不错,木工活很熟。他们翻新房屋和公寓,打墙重修,清理陈年垃圾堆——有活就干。倒不是阿姆斯特丹不是到处都有我们的人,但伊戈尔从不跟他们来往。伊戈尔最近才开始干这种重活。他全身心投入了进去,好像那是某种赎罪。或许他的动力来自这样一种疯狂的念头:自己的满头大汗正在恢复某种平衡,他在这边每筑一堵墙,那边的废墟中就会建起一堵墙,在波斯尼亚或克罗地亚的村庄里,或者任何需要修墙的地方。
生活对我们一直是不错的。伊戈尔出门早,回家也早。回家直奔浴室,冲掉粉尘,换上干净的衣服,撸起衬衣袖子,坐在桌旁。我端上了刚做好的饭菜。我们吃得慢,而且奇怪的是,话说得也少。我们的词语像沙子一样干。我喜欢它们的干。我们或许正在变成荷兰人。据说,荷兰人有要说的话时才开口。
吃完晚饭,我躺在他身旁,吸入他的气味,透过他的皮肤呼吸,就像鱼透过鳃呼吸一样。我让自己的脉搏与他同步,我在他的血管中流动。我起身,隔远了看着他,仿佛不能相信他在这里……我注意到他的面颊上残留着一点油漆,就舔上去,用口水抹掉了它。我用牙齿扒开他的嘴唇,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,吸出一口对我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氧气,又送出一口对他至关重要的氧气。随着这份礼物进入我们的每一根血管,我们都感觉到了令人陶醉的冲动。在那一刻,我们呼吸着提取自无须铭记和无须遗忘的纯净精华。
恐惧偶尔会占据上风。这时,我就会抓起包,披上大衣,然后冲出公寓。伊戈尔不再提出要陪我去了;他让我自己把握,他也知道我会去哪里。通常是海边,那种长长的沙滩。我喜欢深秋和冬令时节荒凉的荷兰海滩。我站在那里,注视着灰色的海和灰色的天,伫立在那里,面对着一堵隐形的墙。接着,我开口说话了,一开始很慢,然后变快,变快,变大声。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,然后它就分叉了:克罗地亚语、塞尔维亚语、波斯尼亚语、斯洛文尼亚语、马其顿语……面对着隐形的墙,我在风中有节奏地把头往前伸,然后说话。我不信神;我不会祷告。我包裹在风中的身影投射在大地上,就像投射到魔术灯里。我,教师,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,说出了我必须说出的话,说出了我的巴尔干祈祷词。我从口中喷出词语,就像乌贼喷出墨汁。我将我的声音寄给无名氏,就像一封瓶中信。将它们抛入风中后,我看到它们在空气中飞舞。我看着它们卷成小管,盘旋着扎进水墙,立即便溶解了,就像是泡腾片……
愿你此生彼世皆受诅咒。
愿你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升起。
愿你被秃鹰蚕食。
愿你从地球上消失。
愿你光脚从荆棘丛上走过。
愿神让你比丝线还要细,比陶罐还要黑。
愿你种下罗勒,收获苦蒿。
愿恶魔折磨你。
愿恶魔喝你的汤。
愿恶魔给你的汤调味。
愿乌鸦啄你。
愿你的血带给你剧痛。
愿你在剧痛中打滚。
愿雷电击中你。
愿闪电击中你,把你从中间劈成两半。
愿你在大地上盲目漫游。
愿蛇咬你的心窝。
愿你像压在树皮底下的虫子一样受苦。
愿浑水将你卷走。
愿你的心脏爆裂炸开。
愿箭射穿你的心脏。
愿你再也见不到阳光。
愿你被一切抛弃。
愿你失去一切,除了你的名字。
愿你的种被根除。
愿你被打成痴呆。
愿你的生活惨淡荒凉。
愿蛇缠住你的手腕。
愿蛇将你生吞。
愿太阳将你活活烧死。
愿你的糖变苦。
愿你的嘴巴和脖子交换位置。
愿你被面包和盐噎死。
愿恶魔让你得病。
愿神将你施加于我的一切施加于你。
愿大海吐出你的骨头。
愿你的骨头长草。
愿你眼中的世界变黑而眼睛变白。
愿你变成尘土和灰烬。
愿神烧掉你的眼睛,留下两个窟窿。
愿你的嘴说不出一个字。
愿你被诅咒。
愿你尿血,尿出沥青。
愿活生生的伤口将你吞噬。
愿你被火焰吞没。
愿你被水淹死。
愿你被烧死。
愿你一动不动地躺在坟墓里一百年。
愿你生时没有配偶,临终不受油膏。
愿你的名字被遗忘。
愿你永远见不到太阳。
愿你浑身腐烂。
愿你被雷霆和闪电击中。
愿你每一天都被杀死一次。
愿你的脸变成草叉。
愿你的根干枯。
愿你爆炸。
愿你舔灰。
愿你变成石头。
愿你的心脏变成石头。
愿你在黑暗中死去。
愿你的灵魂堕落。
愿你逐渐消失。
愿你永远吃不饱。
愿你倒毙路旁。
愿你的喜事变成丧事。
愿你无尽地漂泊。
愿你变聋。愿你变麻木。
愿你一无所有。
愿你从根子里枯萎。
愿你哭着要妈妈的奶。
愿你的骨头从地里拱出来。
愿你被虫子吃掉。
愿你失去你的灵魂和指甲。
愿你永远无人上门。
愿你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。
愿你有盐却没有面包。
愿你变成木头和石头。
愿石头砸在你的心脏上。
愿我的祝福杀死你。
愿你无人知晓。
愿青蛙往你身上尿尿。
愿你一睡不起。
愿我的眼泪杀死你。
愿你的星暗淡。
愿你背井离乡。
愿你的日子变得阴暗。
愿你的舌头发不出声。
愿苦难对你微笑。
愿你抛弃你的骨头。
当我的声带再也发不出声,当我的额头被风吹得麻木,我抛弃了海滩,镇定心神,不留下任何痕迹。荷兰的平原是好的;它们就像当年学校里用的吸墨纸;它们吸收了一切。